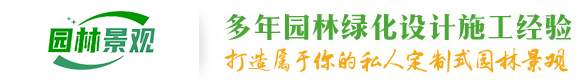健康的城市水环境不仅有助于维持良好的城市生态环境。
增强城市意象,还对生态城市建设与社会和谐发展起到了支撑性的作用。
唐宋时期是成都水系结构演变的重要时期,唐代节度使将成都城沿用千年的“二江珥市”水系结构改变为“二江环抱”。
宋代在此基础上继续开拓,城中贯穿多条渠溪,形成密集的水网,城水关系达到历史上最成熟的状态。
丰硕的水利建设成果也推动了众多西蜀园林的建设,这些园林内部水体形式丰富、趋于自然。
且在城市水系的带动下保持互动关系,共同构成了融于城市的自然生态系统。
基于城市水系的西蜀园林分布特征是城市水系规划建设历史中的典范,于今日仍有传承、借鉴的必要性。
唐宋时期成都水系,指成都遍布的大小水体,包括两江、河、池沼、溪渠四种水下类型。
两江特指环抱成都的郫江与检江;河有穿城而过的金水河、解玉溪、后溪;池沼散布全城,其中以摩诃池、江渎池等最为著名。
两江郫江、检江由战国秦蜀守李冰开凿,属岷江支流,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一部分。
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李)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
两江在成都城东南隅汇合向东流去,改变了城市的治水结构,农业灌溉条件显著提升。
至此成都迈入“水旱从人,不知饥谨,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的新历史阶段。
二江特殊的平面布局也为成都工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西汉时期扬雄《蜀都赋》即有:“两江珥其市,九桥引其流”之语,珥有耳环的意思,形容两江在市集之两侧犹如对称的耳饰,这种景象的形成正是因为当时集市的货物运输与商品制造都依赖于两江水系。
唐末高骈改建成都城,对郫江改道并引其水作西濠,成都城沿用千年的“二江珥市”水系结构变为“二江环抱”,对成都城市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唐末及五代时期成都水利系统虽遭重创,但北宋政府重视成都水利修缮工程,在唐代的基础工程上继续对两江水利系统进行补充与完善。
因此两宋时期依旧保持着唐代两江水利的辉煌,其景象如北宋宋祁诗曰:“两剑作关屏对绕,二江联派练平铺。
此时全盛超西汉,还有渊云抒颂无”。
干渠唐代前期成都城市内部水系营建并不突出,解玉溪是唐贞元年时任四川节度使韦皋在罗城西北隅引郫江水入城形成,并使水系在罗城东南隅再次汇入郫江。
唐宣宗大中七年(853年)时任四川节度使兼成都尹白敏中主持修筑了第二条穿城河道金水河。
其源出西郊郫水联通摩诃池,自西向东与郫江平行横贯城区南部,流至成都东南隅后与解玉溪相汇。
据宋李新《后溪记》可知,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成都知府王觌沿吕大防凿渠旧道。
自城西曹波堰开渠引水东流,渠水跨郫江故道从西门流入城中,分注于城内众多小渠,且位于金水河北,故世人称其为“后溪”。
经过宋代官员对成都水系的梳理和营建,后溪已代替了解玉溪,并与金水河分列于城北与城南,由西向东穿过成都市区,成为城市的两条重要主干渠。
唐宋时期是西蜀园林发展的繁盛时代,营建成果丰硕,各类风姿各异、布局精巧的园林景观遍布城市之中。
以唐宋时期成都城中的官府园林、寺观园林、遗迹园林、私家四大类西蜀园林为主要研究对象。
官宦仕人在唐宋时期是拥有文化与财富的精英阶层,故成都城中分布着数量众多官府园林,象征着封建统治的权威。

另外该类型园林的营建手法与建设规模都是其他类型园林无法比拟的,内涵的艺术价值是该当时西蜀园林的顶峰,与之相关的历史资料也最为详尽。
唐宋时期西蜀地区佛道文化昌盛,促进了寺观园林的兴起。
该类园林虽处于闹市之中,但在城市水系的衬托下依然展现出了清幽静谧的宗教氛围。
遗迹园林多以依托自然基底而建,与城市水系的联系最为密切。
宋时期成都城中还建有其他类型的西蜀园林,但其园林数量较少,且与城市水系的关联度较小,故未纳入研究范畴。
官府园林官府园林是隶属于成都各级官衙、或由官府牵头营建的园林,其管理权与所属权等都归政府所有,但唐宋时期成都普通百姓也享有对部分衙署园林的使用权。
园林常布置于官署内部或临侧,以便官员使用。
除了固有的游赏功能外衙署园林还兼顾政务功能,同时还是官员政余宴集、会宾与燕息等活动的承办地。
唐宋时期成都官员喜与民同乐,因此该阶段西蜀衙署园林的另一个特性是半开放性。
在市井、游赏文化的推动和儒家“与民同乐思想的引导下”,有政府牵头营建通过堤岸、岛屿、廊桥等水利、交通设施与西蜀园林建设相结合的造景手法营建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公共园林。
唐宋时期成都官府园林是与成都居民日常游赏结合最为紧密园林类型,官员们会在特定时间将园林对公众开放。
允许百姓入园游赏娱乐,以彰显官仁,目的是团结民心以促进社会稳定。
依据该时期西蜀衙署园林规模、形态的不同大致将其分为园苑、亭楼两类。
园苑是西蜀官府园林中园林空间相对完整且独立的一种园林类型,园中山水布局巧妙,园林建筑、植物环境的设计都十分精致,能够展现出独具地方特色的园林艺术风格。
唐宋时期西蜀地区官员崇尚游乐之风,几乎每一个州治、县治内或旁侧都营造有特属于政府官员的园苑空间。
西蜀官府园林中亭楼是古代城市空间中标志性景观,承载着功勋纪念、藏书文鉴、军事防御、通达神灵等多种政治与文化功能。
唐宋时期成都官员喜在城中建造楼阁,周边辅以园林绿化使其单独成景,或置于既有园苑中做主景。
以达到宣扬政治权威,彰显官府气派的目的,另一方面楼阁上优越的视野条件使其成为官宦仕人日常饮酒饯别,观景赋诗的重要场所。
成都自秦以来遵循一条北偏东30°的轴线向外扩展,李冰治水所引郫、检两江为西北至东南走向。
为发展城市交通,历代成都城区建设者多开展跨水筑桥工程,并最终形成了成都城街巷空间垂直偏向的格局。
高骈筑罗城时为增加城市防洪功能,其城市平面空间亦顺应水势而建,由西北向东南倾斜。
唐宋时期成都水网密布,城中密集水网多也多依江水流向而建。
成都街巷空间受城市水系的影响,不同于其他大型城市“纵横街衢,整齐划一”的正南北轴线不同,其空间布局多因势而为。
除城区主要街巷空间呈东西向,南北向与河流垂直或平行分布之外,其他街道多呈“人字形”与“回字型”的斜形曲折状。
为完善交通体系,宋代城市中原有的坊墙被全部拆除,城市中开放式的行市与街市取代了旧时封闭式的“市”。
居住区和商业区合二为一,成都大街小巷的交通体系也逐步成型。
成都城内多跨水架桥筑路,因此街道路网呈西北向东南倾斜,垂直于水路网上,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城市通行系统。
总体而言,街巷空间与城市水系走向复合有利于水陆联通,方便了人们的出行与物资的交换,还有助于城市建筑朝阳面布置,体现了成都古代人民“巧借天时,善用地利”的建城智慧。
宋太祖平蜀,以成都为四川节镇。
宋军平定蜀地初期拆蜀宫建材为船,旧宫殿破败不适宜新建成都府治,地方政府不得不另辟府衙。
《益州重修宫宇记》记载:“吕余庆知军府事,取伪太子册勋府为治所。
……使就孟氏文明厅为设厅,廊有楼。
厅后起堂,中门立戟,通于大门。
其中王氏西楼为后楼,楼前有堂……东挟戍兵二营,南有军资大库,库非新建附故书”。
陆游亦有《铜壶阁记》记载:“蒋堂知成都府时,乃南直剑南西川门,西北距府五十步,筑大阁曰铜壶在市区军垒西道之北”。
又有李新《后溪记》载:“由青公堰引水入城,环库至西楼,独府第有水,而城中无水……复凿溪水于备武堂”。
文献中铜壶阁、西楼、阅武堂均与《益州重修宫宇记》中西楼、军资大库相合,由此推断宋代成都的政治中心已迁移至罗城西北部后溪两岸。
商业空间——沿江发展,范围扩大成都自古以来重视商业发展,汉代李冰所建成都七桥(少城南部)一带产生了集工商业聚集区。
交通枢纽区和手工业区为一体的混合商业区。
“汉旧州市在(市)桥南”,依托该区域繁荣的经济与频繁的商业活动,形成了大型的商业空间——南市。
唐玄宗为避安史之乱到成都,在大城东门外新修佛寺——大慈寺,后经发展寺门附近形成“东市”。
韦皋镇蜀后开凿解玉溪并在郫、检两江交汇处建合江亭,并在城东南部万里桥隔江设置“新南市”,至此成都商业空间在前朝基础上开始向南部扩展。
杜光庭记载:“韦皋节度成都,于万里桥隔江创置新南市,发掘坟墓,开拓通道街。
水之南岸,人逾万户,楼阁相属,宏丽为一时之盛”。
唐中晚期以后,成都城中逐渐形成与时令相符的季节性集市。
从该历史时期文人的诗词中可以得知,集市按商品类别的不同区分,其名称有蚕市、花市、米市等。
其中最能体现成都商业经济繁荣的当属“十二月市”,它们并不固定在某一商业区,而是在依托两江沿岸的滨水空间举行。
其择址原因一方面是沿江地区交通发达,商品贩运活动便捷;另一方面滨水地区风景优美,西蜀园林众多,易聚集人气。
沿岸商户密集,楼阁相连,以大慈寺为中心的解玉溪南段、万里桥一带最为繁华。
单一的商贸功能外,该时期的城市商业空间的娱乐功能更为突出,“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的诗句正描绘了当时成都江畔繁华的市井气象。
城市水系影响下西蜀园林选址的特征唐宋时期成都西蜀园林对城市水系有着较高的依存度,并随着城市水系的演进而不断发展。
在园址选择上,城市水系的影响贯穿始终,使成都西蜀寺观园林选址特征呈现出“依水而建,延水而兴”的特征。
西蜀官府园林选址呈现出“借水之胜,因水而迁”的特征;西蜀私家园林选址呈现出“因水而生,以水增色”的特征。
城市水系影响下西蜀园林分布范围的特征总体而言唐宋时期成都西蜀园林分布范围呈持续扩张的形式,城市东、西部西蜀园林分布由极度不平衡到逐渐平衡。
都城市内部西蜀园林分布范围明显扩宽,说明城市内部西蜀园林的营建活动与城郊比较为频繁。
其中官府园林依水相聚,形成组团分布的特征;寺观园林林立江河畔,形成带状分布的特征;遗迹园林因水成园,形成散点分布的特征。
城市水系影响下西蜀园林的游线特征唐宋时期西蜀园林游线的演变与城市水系的发展密切相关。
城西摩诃池段西蜀园林依托城池形态,逐渐构成环状游赏路线;城南检江段西蜀园林利用水的特性而相互串联和引导。
不同景观特征隔江相称,巧构序列,游赏趣味逐渐增加。
城市水系影响下西蜀园林分布形态特征唐宋时期成都城市水系的形态对西蜀园林平面形态的形成产生较大影响。
为保证园林内部水系的供给而选址在江河两岸,园林理水体现了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理水特点,同时又融入仕人文化和西蜀地域特色,其总体特征为“水汇园聚,水疏园散”。
唐宋时期成都西蜀园林立面分布形态的形成、发展与城市水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特殊的城水环境也渗透至城市里面形态之中,形成了“阁楼高耸,以观水景”的立面形态特征。
91秦先生 91秦先生 91秦先生